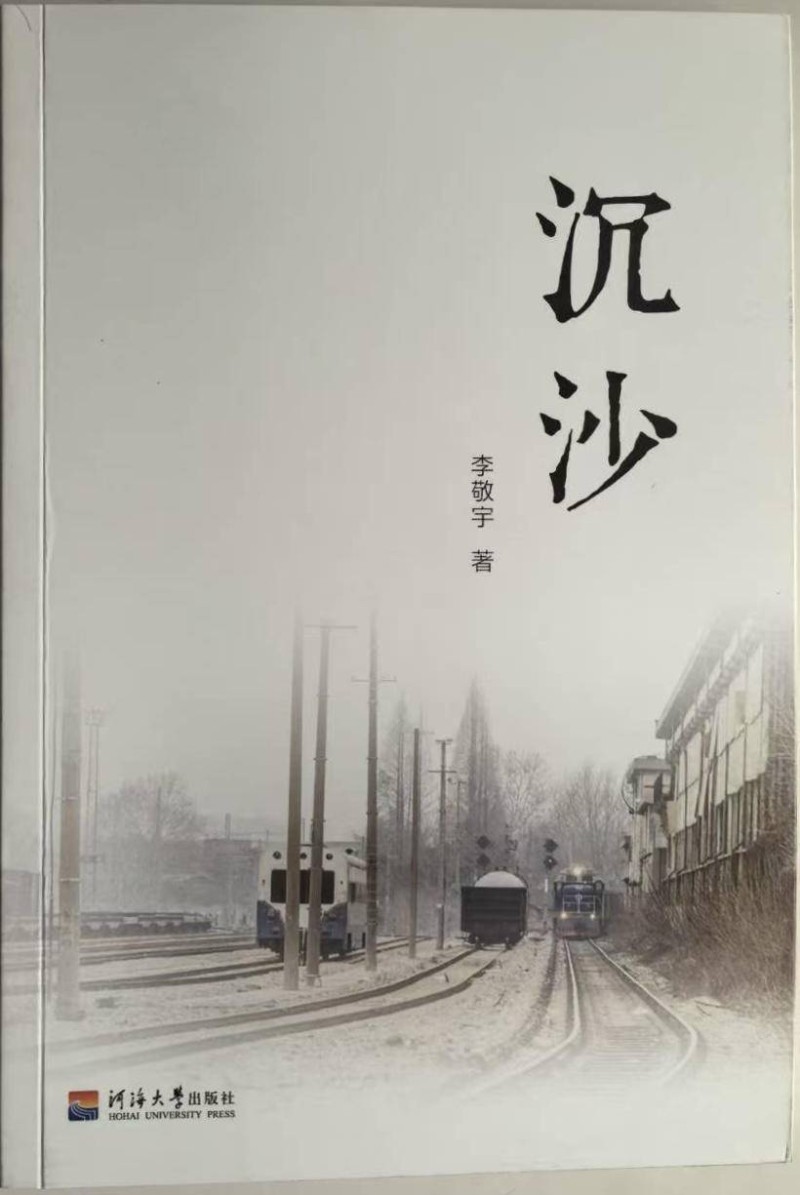作者|拉古拉邁·拉詹(Raghuram G. Rajan)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Katherine Dusak Miller杰出金融學教授。曾任印度央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主任,著有《斷層線》《我行我素》《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等。
? ? ? ? ?羅希特·蘭巴(Rohit Lamba)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客座經濟學助理教授。曾任職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印度政府首席經濟顧問辦公室。
一個國家走向富裕意味著什么?泛泛地講,富裕國家的人均經濟產出更高,有更多的食品(谷物和牛奶等),更多的商品(汽車、服裝、電器、石油和天然氣等),也提供更多的服務(理發、醫療問診、餐飲、住宿、電影和軟件等)。一個國家每個人的產出越多,其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因此,提升收入的關鍵在于提高人均產出,也就是所謂的生產率水平。
顯然,必須有人購買各種產品和服務并為此付款,即對于所有的供給,必須有相應的需求。這里補充一句,“供給”和“需求” 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兩個術語—如果你講話比較快,并且隨意插入這些詞匯,聽眾們就會認為你是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家。有位名叫讓-巴蒂斯特·薩伊的法國經濟學家指出,所有產品出售所得的收入將成為購買這些產品的資金來源。例如農民出售蔬菜, 用收入支付洗衣店的服務,洗衣店老板則用農民支付的洗衣費購買自己消費的蔬菜。雖然實際情況要復雜一些,但生產仍是關鍵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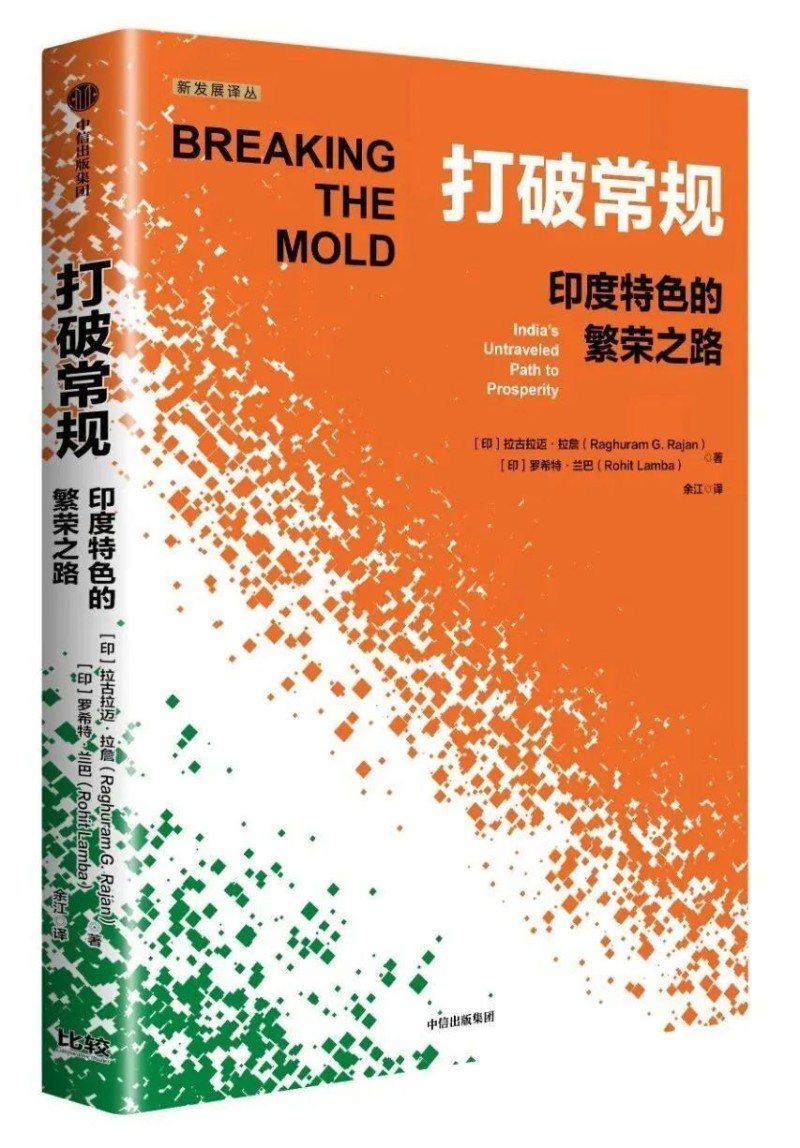
《打破常規:印度特色的繁榮之路》
[印] 拉古拉邁·拉詹 ?羅希特·蘭巴 ?著
余江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7月
更高的收入來自哪里?
如何讓一位勞動者產出更多?首先,利用工具或者機器。在為建筑物打地基的時候,使用鏟子的工人,其進度會慢于駕駛推土機的操作員,后者的工作有強大的機器作為輔助,既更加輕松, 也更具效率。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講,推土機操作員的勞動得到了資本(即推土機)的加持。當然,不知道如何駕駛推土機或者如何操作鏟斗的人反而可能給生產造成破壞,因此勞動者的技能或者說人力資本也影響產出的數量或產品的價值。
還有哪些因素會促進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組織有重要影響。如果這位操作員要負責把土鏟到一個手推車里,將后者推到填埋處,然后用沉重的壓路機把土壓實,再開始鋪設建筑物的地基, 這里的每個生產環節都可能需要獨特的技能,卻沒有一個人能面面俱到。而如果讓推土機操作員把土鏟到卡車里,讓卡車司機把土運到填埋處,由其他人駕駛壓路機將其壓實,最后再由磚瓦匠負責構筑地基呢?采用后面這種組織方式會大大提升生產效率, 不僅因為人們有機器幫忙,還源于勞動者有專業分工,而專家在特定任務方面往往比通才做得更好。偉大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注意到了勞動分工對提高生產效率的好處。當然,這種勞動分工的必要前提是業務量或者說生產規模足夠大。如果我們只是在一個小菜園里搬運泥土,這種分工鏈條將失去意義,因為人太多反而會互相礙手礙腳。
與資本和生產組織方式同等關鍵的是作為其支撐的技術。例如,燃燒效率更高或者動力更強的推土機能讓操作員的勞動創造更大的價值。這里的技術是指增進勞動效率的資本的質量。
最后,如何激勵勞動者以及如何讓產品在經濟體中發揮作用, 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經濟學家把這些問題歸入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制度。其中包括給勞動者的激勵性合同、所有權的性質、物流組織、市場狀況、合同執行、監管乃至獨立司法體系等。在富裕國家,操作員可能是推土機的所有者,由此具備盡量又快又多地挖土的激勵。此外,負責運輸的卡車可以通過高速公路把
挖出的泥土送到海邊,那里的地產開發商利用在線拍賣購買了這些泥土,準備用它們來填海造陸,然后修造一家豪華酒店,大賺一筆。事實上,這里形成了一條通過可執行的合同構成的供應鏈, 能夠高效率地利用各種產品。
相反在貧困國家,這些泥土的現實用途可能很有限。挖出的泥土被堆積在工地旁邊,經常隨風吹散,給周圍地區造成嚴重的粉塵污染,有些還灑落回原來被挖的地方。從掘土挖坑這樣平凡的事情上,就能看到富裕國家的運行效率遠遠超出貧困國家。
那么,絕大多數國民都是農民、牧民或漁民,或者是這些從業者家屬的貧困國家又如何能發展起來呢?如何能變得更加富裕?從上述例子來看,答案似乎很清楚。勞動者需要獲得教育或培訓,使人力資本有所改善;需要有更多設備或者資本的支持;機器設備需要通過技術進步變得越來越好;還需要創立和鞏固各種制度,所有這些的目標都是提升產出和生產率,即單位勞動者的產出價值。
然而不幸的是,要提升農業這類部門的生產率,能做的事情比較有限。化肥、灌溉、拖拉機乃至大型聯合收割機等確實能提高產出,可是歸根結底,土地的數量只有這么多。印度每名農業勞動力在2020 年擁有的平均耕地面積僅為0.67 公頃,而美國的對應數字為46.6 公頃。即便采用最先進的農業技術,印度勞動者也無法從過于狹小的土地面積上生產出太多產品。他們還可以設法提升產品的價值,例如用新鮮蔬菜制作泡菜,或者飼養家禽和山羊等,許多人也的確這樣做了,但與美國人的富裕程度相比仍遙不可及。
在歷史上,勞動者必須從農業向制造業轉移,才能顯著提高生產率。對當今世界的大部分發達國家而言,這曾是個很漫長的過程。有人估計,英格蘭的農業勞動力占比在16 世紀50 年代是63%,到18 世紀50 年代才下降至35%。離開農業的大多數勞動者是在自己家里從事紡紗、織布、縫紉、木匠或鐵匠的工作。工業革命加速了轉化進程,隨著工業體系的進步、蒸汽動力機器的日益普及以及制造業組織的改進,生產效率得以提高。
增長起飛源自良性循環的形成。在許多人脫離農業的同時, 留下的居民可以把土地合并為更大的農場。耕作機械化、種子質量改良、灌溉體系和作物輪作等新技術使勞動力人均產出顯著增加。結果表明,之前雇用的許多農場工人并不是必需的,尤其是隨著尋找勞動力變得越來越困難,農場主會發現更富效率的土地利用辦法。
較為富裕的農場主獲得了更多收入,他們用以添置更精美的服裝、時髦的帽子和鞋子、更好的家具和更大的住房,并消費由城市工廠推出的各類產品。當工廠主變得富裕起來以后,他們把利潤投資于更先進的機器,讓單位雇員生產更多的產品。而當勞動者的生產效率提高以后,他們的薪酬得以增加,也開始為擴大需求做出貢獻。
新的需求在涌現。例如,各地的小酒館讓工廠員工在一天的辛苦勞動后有地方放松,甚至尋歡作樂。于是興起了相應的產業—發酵谷物,蒸餾釀造,然后把啤酒輸送到城市的各個角落。調酒師和女招待的就業崗位也隨之增加。
起初,離開農業、遷入工廠的勞動者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太需要教育。但隨著機器變得日益先進和復雜,工人們需要接受更多培訓,甚至需要掌握數理化領域的一些知識,才能操作、維護和修理那些機器。還有一些聰明的工人在生產現場開展創新, 采用隨機應變的手段來提升機器運行的效率。
此外,隨著工廠規模擴大,經理人、工程師和會計師等新型職位也必須有人來擔任。在服裝形成批量生產之后,消費者要求在樣式上有更多的選擇,于是企業主開始招募服裝設計師。許多原有的工作崗位和新的工作崗位都需要更高的技能及教育水平, 由于高素質勞動者較為稀缺,這些崗位的工資節節上漲。
看到教育會帶來更高的生產率和工資回報后,城市居民開始要求給子女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學校教育,企業主也樂見其成。學校原先只被視為給孩童傳授文明和宗教教義的工具,此時被列入經濟上的要務,成為培訓未來勞動者的重要方式。換句話說,在物質資本擴張的同時,國民的人力資本也在提升,進一步推高了生產率水平。
對長期增長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技術進步。科學家、工程師和工人們一起改進現有機器,發明新的產品,詹姆斯·瓦特和托馬斯·愛迪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經理人則優化生產流程, 提升運行效率,這方面的著名人物有亨利·福特等。
若干國家因此走向了富裕。在1820—1870 年,西歐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年增長率達到了1%~1.3%。與中國和印度在近年來的人均收入增速相比,這非常有限,但與之前5 000 年左右的人類歷史相比,卻是波瀾壯闊的高速躍升。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為何能夠大大加快?
為什么早期的工業化國家不能增長得更快一些?盡管過去也可能實現與如今現代化工廠類似的大規模生產,企業主卻會面臨許多現實約束。例如,他或許沒有足夠的自有資金或融資手段來完成巨額投資,也不敢讓產量大幅超出現有的需求數量,更不敢奢望能夠全部賣出。他必須為需求的逐步增長做好規劃,這來自本國民眾持續的收入提高和支出擴大。而收入和支出的增長則源于投入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持續擴張。當然,像英國這樣的早期工業化國家在當時擁有印度等殖民地,可以吸收其制成品。
然而貧困的殖民地民眾購買殖民者產品的能力從一開始就很小, 而隨著機器制造的進口產品排擠本地手工產品,殖民地民眾變得越發貧困,購買力進一步縮小。所以從長期看,帝國主義并非可持續的需求增長的源泉。
技術進步可以顯著提高產出和收入增長的速度,依靠更先進的縫紉機,制衣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收入隨之增加,并能夠把更多資金用于食品和娛樂消費。但由于這些國家使用的已經是當時最好的技術,更先進的技術還有待發明創造,因此處于知識前沿的創新速度則相對較慢。
然而近年來,我們看到部分經濟體取得了極其出色的增長成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若干亞洲經濟體,以日本為首,之后有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臺灣,更近一些的則是中國大陸(印度的情況稍后再做討論)。
記者兼作家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撰寫的頗具啟發性的著作《亞洲大趨勢》(How Asia Works)試圖解釋:在20 世紀下半葉,亞洲各經濟體怎樣以不同于傳統的方式實現了從農業向制造業的轉型,尤其是政府在其中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轉型的起點是土地改革,把土地所有權(或者中國采用的承包經營權)分配給耕種者。這讓小農戶得以實現繁榮,生產出能夠用于制造業的剩余產品。但政府意識到,如果制造業必須等待國內產品需求的積累,則會在較長時間里局限于較小的規模和較低的生產率。
不妨設想下,有個擅長制造高頂禮帽的國家。如果想通過國內需求來實現較大的規模,就需要收入水平有很大提升,讓上層社會的人舉辦大量舞會和賽馬之類的活動,并把禮帽作為標配。這要等待很長的時間。但如果這個國家把目標瞄準富裕國家,則可以滿足對高頂禮帽大量現成的需求。
因此,制造業的規模經濟可以借助發展中國家擁有的初始比較優勢,例如較為富裕的工業化國家已經失去的廉價勞動力,再通過占領世界市場來實現。政府可以鼓勵生產商專注于出口部門, 尤其是需要大量低技能或中等技能的產業,包括紡織品、皮革制品、玩具和電子產品組裝等。在此類部門,來自富裕國家的需求會彌補本地需求的不足,讓增長和生產規模不再受制于本地的低水平需求。
這些經濟體也不會受到技術水平的拖累。由于發展中的亞洲經濟體并沒有處在技術前沿,它們可以購買、模仿、租用甚至竊取先進技術,無須開展創新。例如在一開始給制衣工人購買基礎縫紉機,然后再引入更為先進的類型。由于工業化國家已經完成了必要的創新,所有這些技術都是現成可用的。所以,相比前沿國家的增長,追趕型增長更容易,速度也更快。
制造業的生產率不會保持不變。隨著反復練習,工人的技能將提高,每小時產出的數量會增加,差錯率和浪費率會減少,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作干中學。另外,隨著規模擴大,自動化水平會提高,例如用機器來縫制紐扣以取代人工,這會降低成本, 提高生產率。經理人也在干中學,尋找激勵員工的更好辦法,調整生產線,改善供應和運輸的物流管理。外國生產商來本地建設基地,會把它們的生產實踐帶進來,讓國內企業通過模仿來學習提高。
隨著工人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提升,制造商會轉而生產更復雜的產品,例如照相機、摩托車、汽車和機械等,把低技能制造業交給發展階梯上后來的其他國家。逐漸靠近技術前沿的國家將開始啟動自己的研究開發,與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將被縮小,像日本的照相機、韓國的電視機和中國的電動汽車還在世界上占據了領先地位。
最后,有競爭力的出口導向型產業獲得的先進操作經驗會被推廣到整個制造業部門,乃至經濟中的其他部門。需要即時庫存與可靠交付的出口商會要求改善物流和運輸服務(例如要求更好的卡車維護),以減少意外延誤等。隨著物流和運輸的改善,各地的房地產開發商就能更有效地采購原材料,加快住房建設。用專業術語來講就是,生產率的進步不會停留在出口導向產業,而是會擴散到建筑業等其他經濟領域。制造業確實會成為通向富裕的階梯。
亞洲的出口導向型增長加快了勞動力在產業部門之間的轉移, 但這一轉型與富裕國家過去經歷的情形依然類似。首先是制造業的擴張,吸引了農業勞動力,制造業在國家經濟總產出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制造業的強勁生產率增長會提高勞動者的收入, 而隨著民眾變得更加富裕,他們開始要求更多的服務。對貧困國家而言,大部分服務是在家庭內部發生的,人們準備自家的飲食, 讓家人幫忙理發等。當某些人發財致富之后,他們會聘用廚師, 找理發師給自己服務。當整個國家變得更富裕之后,家庭用人會變得較為昂貴。當人們不想自己做飯的時候,他們可以去餐廳享受美食。簡單地說,制造業的生產率進步會提升對服務的需求, 并最終減少制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
服務業的增長將隨之加速,并把勞動者從農業和制造業中吸引過來,減少它們所占的勞動力份額。服務業最終將成為整個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就業領域。如果把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就業比重當作人均收入的函數,它起初會上升,此時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制造業,之后則會下降,此時勞動力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通常來說制造業的勞動力占比只有在一個國家變得相當富裕之后才會下降,而且鑒于制造業崗位的生產率水平較高,它在經濟產出中的占比不會下降得那么快。
印度的表現如何?
把一個國家為商品和服務支付的所有收入累加起來,我們就能得到該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再將GDP 除以這個國家的全部人口,我們就能得到該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專業術語中是人均GDP。
1961 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為86 美元,韓國為94 美元, 中國為76 美元。印度處在這一批極端貧困國家的中間位置。如今, 印度人均收入水平約為2 300 美元,中國約為12 500 美元,韓國約為35 000 美元。印度不再居于中流,而是遠遠落在后面。印度人對上述統計數據可能有三種直接反應。第一種當然是:這樣的對比不公平,我們選擇了人類歷史上兩個最成功的經濟增長案例來跟印度做對比。第二種反應是沮喪:印度怎么會搞得這樣糟糕? 第三種反應是辯護:印度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把維持多元化國家的穩定和民主作為優先事務,而非不計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這三種反應都有某些合理之處。
例如,我們確實選擇了兩個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來做對比,如果是與其他國家相比較,印度的表現并沒有那么糟糕。在1980— 2018 年,印度人均GDP 的年均增速約為4.6%,十年期平均增速也從未低于3%。如果在這38 年中篩選年均增長率不低于4.5% 且任何連續十年期平均增速不低于2.9% 的國家,會發現只有9 個國家符合標準。并且除印度之外,其中只有博茨瓦納基本上維持著民主制度。
增長故事中還有一個側面值得關注。我們之前提到,制造業的勞動力占比通常會在一個國家發展的某個時點見頂,然后下降。不過美國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自1990 年起,在若干非洲和拉美國家,制造業的勞動力和總產出占比已開始下降。該現象的出現遠遠早于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歷史上制造業份額開始走低的通常水平。羅德里克認為,印度的情形同樣如此,制造業的勞動力占比自2002 年起已開始下降。盡管人們對于印度是否已出現去工業化仍存在爭議,但毫無疑問, 與發展中國家的典型情況相比,印度的服務業吸收了更多脫離農業的勞動力,而制造業的勞動力占比維持相對平穩的狀態。對印度這樣的后發工業化國家而言,這到底是一種缺陷還是一種特色, 我們將在之后的幾章中展開討論。
但無論怎樣選取數據,很明顯的一點是,印度是制造業出口游戲中的遲到者,直至20 世紀90 年代早期才啟動相應的改革。印度在此之后的經濟增長顯然受益于出口的擴張,其中既有制造業,也有服務業。可是,印度為什么還沒有建立起更大的制造業部門?它更擅長何種類型的制造業?這是下面我們要探究的問題。
—End—
本文選編自《打破常規:印度特色的繁榮之路》,注釋從略,題目為編者所擬,推薦閱讀。該文由發布,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內容參考,不得用于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轉載行為都需留言咨詢,其中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