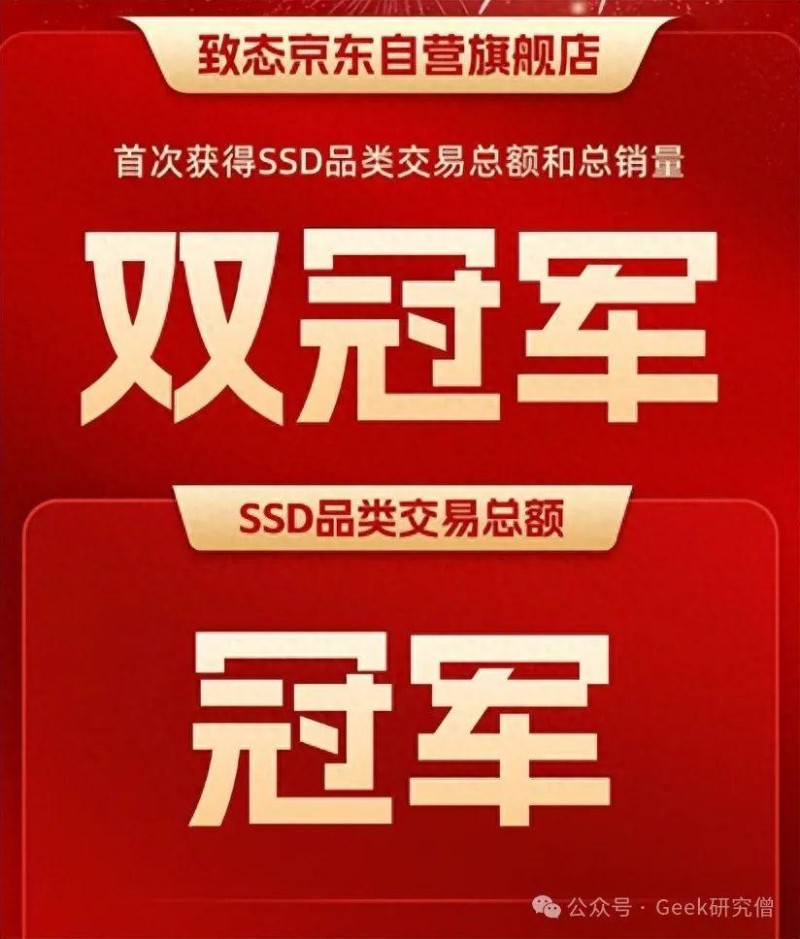繼《江南繁荒錄》《做壺》《包漿》后,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學者作者徐風推出長篇系列散文《江南器物志》,該書經《收獲》雜志“江南器物”專欄連載,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此次,徐風將目光拓展至更廣闊的江南器物譜系,以“器隱鎮”為文學道場,從科舉、稼穡、節慶、風俗、嫁娶、餐飲、庭院、家具、服飾、舟車、禮品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書寫南方溫潤又激烈的山水間那些人與物,器與神。
“器物是人們無聲的忠實陪伴,它儲存過往,冷觀當今。”不同于博物館櫥窗里的靜態陳列,徐風筆下的器物始終與人的體溫相依偎,通過追究民間器物的起始、傳承、流變,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質與文明菁要,和中國文化在江南土壤中的根系與旁通。作者以十年田野調查為根基,行走于多個江南文化現場,通過紀實與推演交輝的“器物志文學”敘事,讓沉默的器物開口講述自己的前世今生。
舉人的竹編考籃,毛竹里揉進汗漬的鹽霜;素娥們的織布土機,纏繞著未盡的情絲;當鋪門前的青石板路,凝固著無數人生的輕與重。
如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謝有順所言,“物質即記憶,一物一世界,通過這些與器物相關的風華、執念、恩德、慈悲,徐風寫出了一個時代的情義,一個地方的靈魂,以及那些至今難以釋懷的心痛與歡悅。”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說世,打撈“非遺”精魂,在器物的綿延意象中,《江南器物志》不僅復原了江南傳統生活,也讓當下中國人的生活得到了豐盈的折射,最終指向器物背后生生不息的中國精神與生活美學。
以物觀世:“器物志文學”搭建江南版“清明上河圖”
《江南器物志》以一座江南古鎮“器隱鎮”為場域,用十個故事單元切入古鎮民生的方方面面,通過對諸多器物的聚焦,開創性地建構了“器物志文學”的概念范式。
“科舉、稼穡、節慶、風俗、嫁娶、庭院、舟車、服飾……都是中國文化語境里永不破敗的肉身;俗世生活中的菜單、食譜、藥方、茶道、風水、方術、古玩、字畫,亦是中國古人精魂里不可磨滅的諸般星宿,乃至茶館、酒樓、當鋪、錢莊、塾館、文廟、診所、會館、別院……都是人世間必不可少的驛站港灣。”
該書是徐風融匯地方風物與個人思辨的成果,也是他在“江南器物”方向的深耕之作、創新之作。如評論家汪政所言,《江南器物志》既是徐風器物書寫的上階突破之作,更是思索江南風土與歷史文化的深沉之作。
在徐風筆下,官人、細民、文士、商賈、民女、捐客、丐徒輪番登場,由人寫器,由器觀世。他深諳器物與生活的共生關系,每一件器物都成為開啟特定社會空間與生活紋理的鑰匙。從龍骨水車到犁耙鋤釬,從碗碟盤盞到鼎龕鬲匜,作者在溫習稻飯羹魚里的古老器具之余,挖掘出其中的歷史、文化、掌故、情感,想象著器物背后的人與中國文化精神,試圖在人與物、器與神之間,“構建一條神性通道,去汲取一隅之豐沛,與廣袤的世界進行無處不在的對話。”
作家的“小小的野心”,起始于用文字搭建、還原的一座煙火漫卷的江南古鎮。這座“器隱鎮”有著驚人的真實肌理——打谷場上的梿枷,在麥收季節里“吃”得滿嘴油光;得義茶樓的紫砂壺里,漂浮著龍井的茸毛;當鋪柜臺的柵欄里,晃動著大掌柜老鶴般清瘦的身影;細竹刀游弋時,竹編考籃上的竹片跳來晃去;合歡桌桌面和桌腿的角牙間,暗藏栩栩如生的花果紋——借助田野調查、名物研究、史志爬梳、古籍鉤沉等種種考據,每件器物的形制都被精確復原。這種近乎執拗的考據背后,是三年間走訪八座博物館、翻閱百余冊方志的積淀。
徐風認為,一個作家無論從事何種文本寫作,都應該與田野調查建立一種緊密的關系,忠于事實的文字,它不會撒謊,無論歲月更替、人事代謝。從真實的場域和細節中,那些“隱藏于江南廣袤民間的風土情懷,古老傳器中未被忘卻的俠義肝膽”也漸次浮現。
敘事革新:器物長河里的中國精神
全球化浪潮中,傳統器物面臨著“博物館化”的危機。但徐風沒有停留在懷舊式的詠嘆,而是通過器物演變的脈絡,探討傳統如何參與現代生活建構。這些古老的器物智慧,在當代設計中正煥發新生。江南器物始終流淌著鮮活的生命力,在這種新舊交融的生機之間,“徐風打撈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仍在呼吸的生活儀式。”如果說器物是中國文化永不破敗的肉身,而使用它的人們,則是讓血脈持續搏動的靈魂。
徐風筆下的江南器物,最終指向了現代人需要共同關心的命題:在物質豐裕的時代,更需要懂得“敬物惜福”的生活藝術。所謂文明,不過是人與物之間那份相知相惜的溫柔。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