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原平方(文化學(xué)者)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duì) / 李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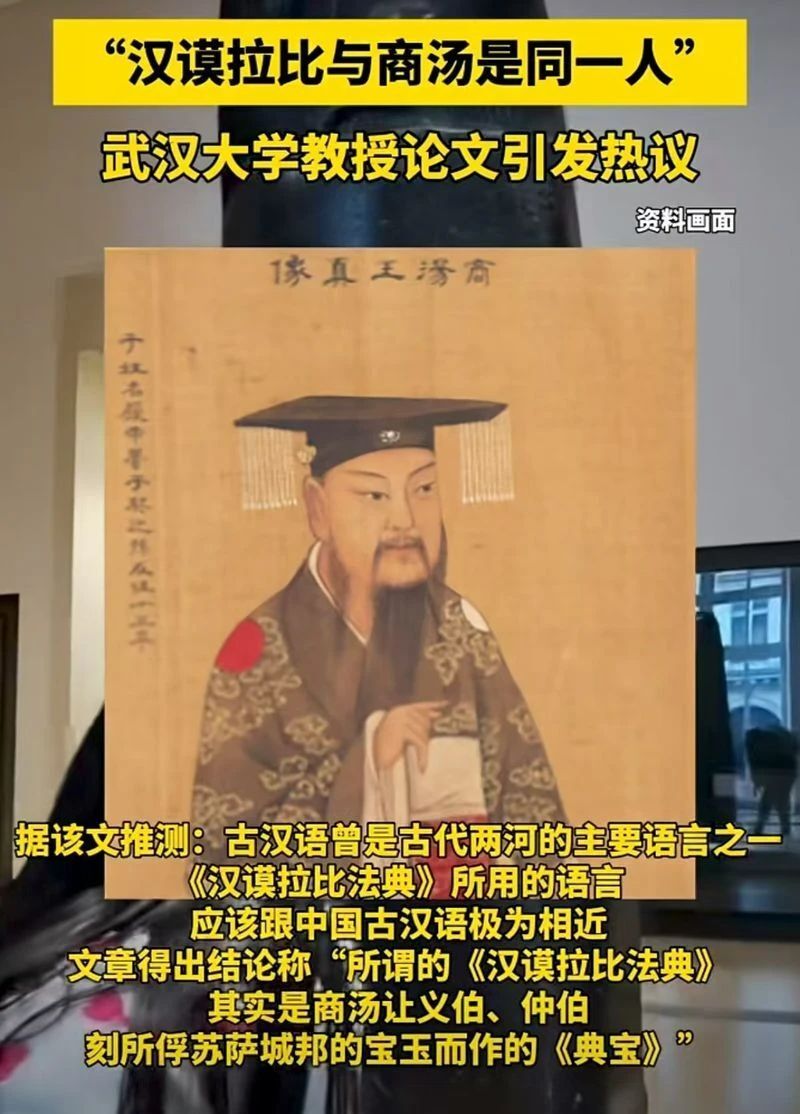
▲一篇2007年刊發(fā)于《武漢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論文《〈漢謨拉比法典〉與商湯關(guān)系新論》引發(fā)圍觀。圖/華聲在線視頻截圖
近日,據(jù)澎湃新聞報(bào)道,一篇2007年刊發(fā)于《武漢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論文《〈漢謨拉比法典〉與商湯關(guān)系新論》引發(fā)圍觀,原因在于該文所提出的“漢謨拉比與商湯是同一人”這一觀點(diǎn)不僅足夠大膽,也過(guò)于牽強(qiáng)附會(huì)。
作者先推測(cè)古代兩河流域也使用古漢語(yǔ),“《漢謨拉比法典》所用的語(yǔ)言應(yīng)該跟中國(guó)古漢語(yǔ)極為相近,或者漢謨拉比本人就是中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帝王,只不過(guò)是由于英國(guó)人把巴比倫語(yǔ)翻譯成英語(yǔ),再?gòu)挠⒄Z(yǔ)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yǔ),造成了極大誤會(huì),導(dǎo)致我們中華后輩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shí)一家人”。
再羅列漢謨拉比和商湯在歷史文獻(xiàn)中的事跡之后做出假設(shè)性結(jié)論:“所謂的《漢謨拉比法典》,其實(shí)是商湯讓義伯、仲伯刻所俘蘇薩城邦的寶玉而作的《典寶》……”單從論述上而言,作者等于用一系列推測(cè)和假設(shè),來(lái)證明“漢謨拉比與商湯是同一人”。
任何大膽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都必須建立在扎實(shí)的論證基礎(chǔ)之上,脫離了實(shí)證支撐的“創(chuàng)新”,不僅無(wú)法推動(dòng)學(xué)術(shù)進(jìn)步,反而可能偏離學(xué)術(shù)研究的正軌。應(yīng)該說(shuō),這篇論文引發(fā)的爭(zhēng)議,本質(zhì)上即反映了學(xué)術(shù)探索中想象力與實(shí)證精神之間的平衡問(wèn)題。
毋庸諱言,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需要想象力,但這種想象力并非天馬行空的奇思妙想。在社會(huì)學(xué)家米爾斯看來(lái),所謂想象力,就是要求研究者能夠在紛繁復(fù)雜的現(xiàn)象中發(fā)現(xiàn)隱藏的聯(lián)系,在已有知識(shí)框架中找到突破的空間,然而這種能力的前提是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深入了解和對(duì)既有成果的全面把握。
歷史研究的想象力,更需要植根于具體的歷史語(yǔ)境,尊重不同文明的發(fā)展脈絡(luò)與文獻(xiàn)記載的基本事實(shí)。漢謨拉比作為公元前18世紀(jì)古巴比倫的統(tǒng)治者,其歷史形象由兩河流域的銘文、法典和考古發(fā)現(xiàn)共同構(gòu)建。相較來(lái)說(shuō),商湯作為中國(guó)商代的開(kāi)國(guó)君主,其事跡則見(jiàn)于《尚書(shū)》《史記》等文獻(xiàn)及殷墟考古成果。
二者分屬不同的文明體系,在時(shí)間、空間、文化譜系上至少目前還沒(méi)有發(fā)現(xiàn)可靠證據(jù)表明存在關(guān)聯(lián)。所以,這種脫離基本歷史語(yǔ)境的“關(guān)聯(lián)想象”,顯然違背了學(xué)術(shù)想象力的科學(xué)內(nèi)涵。
同時(shí),“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也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基本準(zhǔn)則,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可以說(shuō),“大膽假設(shè)”為學(xué)術(shù)探索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小心求證”則確保這種探索不至于偏離科學(xué)軌道。
歷史研究尤其強(qiáng)調(diào)證據(jù)的充分性與邏輯鏈條的完整性,更重視“孤證不立”的基本規(guī)范,并且各種拿來(lái)論證觀點(diǎn)的證據(jù)必須經(jīng)過(guò)嚴(yán)格的考辨與驗(yàn)證。
反觀這篇爭(zhēng)議論文,僅有的三條參考文獻(xiàn)既不能涵蓋兩種文明研究的核心學(xué)術(shù)成果,也沒(méi)有引用原始文獻(xiàn)或考古報(bào)告,如此薄弱的文獻(xiàn)基礎(chǔ)明顯無(wú)法支撐這樣顛覆性的結(jié)論。真正的學(xué)術(shù)求證,應(yīng)當(dāng)是對(duì)史料的細(xì)致梳理、對(duì)矛盾的合理解釋、對(duì)證據(jù)的交叉驗(yàn)證。而缺乏充分求證的大膽假設(shè),恐怕只能停留在假說(shuō)層面,很難成為被學(xué)界認(rèn)可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
值得注意的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底線還要求尊重歷史的客觀性與嚴(yán)肅性,不能將歷史視為可以隨意解構(gòu)或重構(gòu)的文本游戲。
歷史人物的存在、文明的發(fā)展都有其特定的時(shí)空背景和物質(zhì)載體,任何學(xué)術(shù)探索都應(yīng)當(dāng)在尊重這些基本事實(shí)的前提下進(jìn)行。漢謨拉比與商湯作為不同文明中的重要?dú)v史人物,其形象早已被各自的文獻(xiàn)記載、考古發(fā)現(xiàn)所定格,將二者強(qiáng)行等同,本質(zhì)上是對(duì)歷史主體性的忽視,也是對(duì)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背離。
這樣的私人研究也許能滿足研究者自己的好奇心,可對(duì)歷史學(xué)科的發(fā)展并無(wú)多少實(shí)質(zhì)助益,公開(kāi)發(fā)表甚至可能誤導(dǎo)公眾對(duì)歷史的認(rèn)知。在這一意義上講,對(duì)明顯缺乏嚴(yán)謹(jǐn)論證的論文,作為學(xué)術(shù)傳播平臺(tái)的期刊,其把關(guān)審核不應(yīng)失守。
一篇論文的問(wèn)世,往往需經(jīng)歷收稿、初審,甚至匿名評(píng)審及期刊終審各環(huán)節(jié),目的就是嚴(yán)格校驗(yàn)論證的嚴(yán)謹(jǐn)性、論據(jù)的有效性、結(jié)論的合理性以及研究方法是否規(guī)范等等。這樣看來(lái),能夠發(fā)表這樣匪夷所思的所謂“創(chuàng)新”文章,《武漢科技學(xué)院學(xué)報(bào)》怕難辭其咎。一篇2007年刊發(fā)的論文,現(xiàn)在爆出如此有失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的問(wèn)題,也讓人懷疑期刊本身的“水分”有多大?對(duì)此,相關(guān)方面有必要起到問(wèn)責(zé)機(jī)制。這是審核失職,還是涉及利益輸送,必須調(diào)查清楚,并循跡問(wèn)責(zé)。
歸根到底,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過(guò)程,大膽的想象與嚴(yán)謹(jǐn)?shù)那笞C缺一不可。大膽創(chuàng)新不等于放任空想,勇于探索不等于放棄規(guī)范。
而歷史研究激動(dòng)人心的地方,在于通過(guò)對(duì)史料的細(xì)致解讀和對(duì)證據(jù)的小心求證,不斷接近或發(fā)現(xiàn)歷史的真相。反之,任何試圖跨越實(shí)證基礎(chǔ)的“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都難以經(jīng)得起時(shí)間和學(xué)界的檢驗(yàn),也容易讓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研究走向獵奇式、娛樂(lè)化。
因此,只有將想象力置于科學(xué)論證的軌道之內(nèi),讓創(chuàng)新建立在扎實(shí)的史料基礎(chǔ)之上,學(xué)術(shù)研究才能真正發(fā)揮其傳承文明、啟迪智慧的作用,避免淪為架空歷史的無(wú)稽之談。
值班編輯 王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