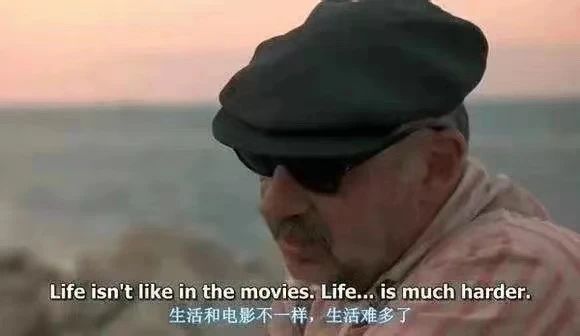「這仿佛為我們制造出一個(gè)超然的外部視角——一個(gè)不帶指責(zé)、不必回應(yīng)的“虛擬照護(hù)者”。」
>>>
“小人建過(guò)山車就是為了嚇自己一跳。”
“有的小人定期裝飾自己的指甲蓋。”
“小人吃飽了就屁顛屁顛去拉屎。”
“從上帝視角看,一群小小人被苦難絆住就哭著說(shuō)不活了,真的挺萌。”
(“上帝視角看人類”部分文案)
#上帝視角看人類#把生活切換到一個(gè)微縮景觀中。這種抽離自身、以觀察者甚至“造物主”般的視角,將人類自身(包括行為、生理、社會(huì)規(guī)則等)當(dāng)作客體進(jìn)行審視、描述和調(diào)侃。
比如“拿一個(gè)塑料條條假裝自己的睫毛”“飛機(jī)上人類齊齊睡去又在放飯的時(shí)候都醒來(lái)好像等待喂食的倉(cāng)鼠”……人類自己就像一個(gè)被投放進(jìn)布景中的小小角色,一邊忙碌奔跑,一邊不知為何登場(chǎng),而世界則像一個(gè)巨大的劇場(chǎng),充滿了旁觀者視角、隱形劇本與NPC任務(wù)。
這類話語(yǔ)引發(fā)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yīng)。一種聲音認(rèn)為,這種表達(dá)方式讓日常變得有趣,是在疲憊生活中的自我?jiàn)蕵?lè)與解壓;另一種聲音則批評(píng)它是“咯噔文學(xué)”或“嬌妻文學(xué)”的變體,把真實(shí)的苦難輕描淡寫(xiě)為“小人被絆住”,是一種對(duì)痛苦的娛樂(lè)化、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逃避。
(部分網(wǎng)友認(rèn)為“上帝視角”是“咯噔文學(xué)”)
爭(zhēng)議的核心,其實(shí)不止是表達(dá)內(nèi)容,而是我們?nèi)绾卧诠部臻g中安放自己的情緒。“上帝視角”輕盈調(diào)侃式的表達(dá)成為一種折中的語(yǔ)言策略——
將“我”轉(zhuǎn)化為“小人”,歸于“人類”的集合體,個(gè)體既參與其中,獲得了自嘲與喘息的自由;又得以抽離,在語(yǔ)言中虛構(gòu)一個(gè)自我關(guān)照的空間,哪怕短暫、脆弱,也足以包裹當(dāng)下的自己。
在“上帝視角看人類”的文案中 “吃、喝、拉、撒、睡”是主線任務(wù),其上附加小人們“自得其樂(lè)”或“崩潰叫喊”的支線任務(wù),一切責(zé)任或身份都被暫時(shí)擱置。
微縮提供了一種抽離的觀看方式。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人類早已不再是簡(jiǎn)單的“動(dòng)物”,但也沒(méi)有變得“完全理性”。在以效率為核心的工作制度、充滿表演性的社交期待,以及邊界模糊卻控制感強(qiáng)烈的公共空間規(guī)范的層層規(guī)訓(xùn)之下,我們逐漸忘記了作為一個(gè)“有機(jī)體”的生存方式:困了睡、急了跑、餓了吃。
具身性理論指出,人的情緒與意識(shí)并非懸浮于身體之上,而是與感知深度融合。當(dāng)身體被迫讓位于效率,思維也隨之脫節(jié),人類成為時(shí)刻運(yùn)作的機(jī)器,壓抑與倦怠便成為日常底色。
(真實(shí)故事計(jì)劃《困在腸易激中的高中生》網(wǎng)友評(píng)論)
這種壓抑并不少見(jiàn)。2020年,初中生與高中生腸易激綜合征檢出率分別高達(dá)13.43%與26.85%;而互聯(lián)網(wǎng)討論中,絕大部分網(wǎng)友都表明,自己在成年之后仍會(huì)在重要場(chǎng)合腸胃應(yīng)激。這些并非真正的病,而是一種情緒和壓力無(wú)法排解后的“軀體抗議”。
而在“上帝視角”下,人類被還原為“小動(dòng)物”:無(wú)需解釋行為,不承擔(dān)責(zé)任,可以理直氣壯地吃、玩、睡和崩潰。
博主@菇菇米Gugumi因“小人”和“小孩”系列視頻走紅。在她的“小人系列”中,小人用化妝刷掃地,在衛(wèi)生紙卷上跑步,用花生米壓腿健身——日常行為被微縮化處理,生活變成了冒險(xiǎn)。
(@菇菇米“小人”和“小孩”系列視頻)
她扮演的“小孩”角色則總在比劃著小手,一刻不停地表達(dá)情緒:為才藝表演緊張,對(duì)酒店小牙膏著迷,打開(kāi)電器時(shí)充滿好奇……小孩的無(wú)聊,就是那種“總找不到地方安放的十個(gè)手指”,而這些瑣碎感受在鏡頭中都被認(rèn)真地對(duì)待。
許多成年人在觀看后“安心地緩緩展開(kāi),緩緩下沉”,仿佛回到了那個(gè)牛奶打翻就要哭、發(fā)呆一整天也不會(huì)被催促的童年。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長(zhǎng)期被壓抑的基本需求:想要被細(xì)心照顧,想要被無(wú)條件理解。
(網(wǎng)友對(duì)@菇菇米Gugumi的安利文案)
在更廣泛的年輕一代的認(rèn)知中,和貓狗相處的養(yǎng)寵經(jīng)驗(yàn)也被轉(zhuǎn)化為一種柔性的對(duì)照——人類意識(shí)到,為寵物準(zhǔn)備慢食碗、設(shè)計(jì)玩具“豐容”以及每日必要的放風(fēng)遛彎,其實(shí)是對(duì)它們節(jié)律的體貼;而這份體貼若回流向人類自身,則是一種遲到卻必要的理解。
這套“擬物化”敘事并非沒(méi)有爭(zhēng)議。
“第一次活,手忙腳亂,一點(diǎn)小事就想死,是正常人類的可愛(ài)反應(yīng)機(jī)制。”在贊同者眼中,這是對(duì)自己脆弱狀態(tài)的寬容;在批評(píng)者看來(lái),這無(wú)異于把真實(shí)痛苦娛樂(lè)化、可愛(ài)化,甚至帶有“自嬤”的意味——用嗲萌、順從、無(wú)害的方式包裝經(jīng)歷,以弱者姿態(tài)把痛感處理成撒嬌,以便于他人接受,同時(shí)也掩蓋了應(yīng)有的抵抗強(qiáng)度。
(部分網(wǎng)友認(rèn)為“上帝視角”令人不適)
“自嬤”成為貶義標(biāo)簽,反映了當(dāng)下人們對(duì)“二手情緒”的敏感。在公共空間里,我們不僅要應(yīng)對(duì)自己的悲傷和崩潰,還要不斷吸收他人的情緒投射。
但若將“小人劇場(chǎng)”的話語(yǔ)完全歸為“自我物化”,則未免失之偏頗。它更多是一種極限情境下的情緒調(diào)適方式。文化理論中的“弱理論”主張:用低強(qiáng)度、碎片化、非線性的方式理解復(fù)雜現(xiàn)實(shí)。這種“弱姿態(tài)”并非妥協(xié),而是一種現(xiàn)實(shí)下更節(jié)能的生存策略。
英國(guó)作家西蒙·加菲爾德在《把世界裝進(jìn)火柴盒:微縮的歷史》中寫(xiě)道,人類對(duì)微縮世界的癡迷,包含秩序和掌控的渴望。搭建生態(tài)箱、挖螞蟻洞、拼樂(lè)高、玩《我的世界》……這些微縮行為讓我們?cè)诂F(xiàn)實(shí)的不可控中,找到一種仿佛“造物主”的安全感。
(微型立體模型大師田中達(dá)也作品)
它不求根本解決問(wèn)題,卻能以最低代價(jià)緩解情緒內(nèi)耗,為個(gè)體爭(zhēng)取一點(diǎn)喘息的余地。但“自嬤”是否真的能抵抗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苦難?這仍是一個(gè)值得追問(wèn)的問(wèn)題。
人們的廣泛共鳴也暴露了一個(gè)事實(shí):我們正處于一個(gè)照護(hù)機(jī)制失效的社會(huì)。無(wú)論是親密關(guān)系、職場(chǎng)制度、公共空間還是情緒互助網(wǎng)絡(luò),越來(lái)越多的個(gè)體感到無(wú)處可逃、無(wú)處可托。
“上帝視角”沒(méi)有提供什么深刻洞見(jiàn),但它可以被所有人套用在任意一種狼狽、無(wú)措、微弱的處境上。人類社會(huì)千百條或成文或不成文的規(guī)訓(xùn)一下子不存在了,腦袋空空,世界安靜,渺小甚至輕盈。
也許,“上帝視角”是人類在現(xiàn)實(shí)中找不到出口時(shí),對(duì)照護(hù)空間的一種虛構(gòu)嘗試。
這種語(yǔ)言并不是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語(yǔ)境中。從“嬌妻文學(xué)”到“鼠鼠文學(xué)”,再到今天的“小人劇場(chǎng)”,我們始終在為真實(shí)的苦難尋找一種可承受、可言說(shuō)的表達(dá)方式。
(“自嬤”文學(xué))
當(dāng)傳統(tǒng)意義上的“被關(guān)心”“被照料”變得稀缺甚至尷尬,在這種情境下,語(yǔ)言開(kāi)始承擔(dān)起“替代照護(hù)”的功能。“上帝視角”便是其變體:一個(gè)抽離的、無(wú)指責(zé)的觀察者,一種溫和的語(yǔ)言策略。
娛樂(lè)式的自我觀察與自嘲因此得以超越個(gè)體私語(yǔ),上升為一個(gè)“從云端俯瞰”的公共表達(dá)形式。
語(yǔ)言雖然無(wú)法改變現(xiàn)實(shí),卻可能激活某些遲到的理解和體察。在鼠鼠文學(xué)中,我們理解了安陵容,也理解了“惡毒女配”;在嬌妻文學(xué)中,我們讀到了“晚晚”,也看見(jiàn)了她背后更立體的女性困境。在“養(yǎng)寵”過(guò)程中,許多人開(kāi)始意識(shí)到自己是一個(gè)充滿掌控欲的“家長(zhǎng)”;而在“小人劇場(chǎng)”中,更多人第一次意識(shí)到,生活的主線其實(shí)應(yīng)該是“吃喝拉撒睡”——那些一直被效率社會(huì)所遮蔽、被忽視的基本需求。
引入鼠鼠,引入時(shí)光機(jī),引入自然生靈,引入“上帝視角”,都是一次次試圖重新把握住當(dāng)下的努力。它們消解的不只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也是在消除一種深藏的自我審判:脫離了表面的感動(dòng)、想象與厭棄之后,我們或許終于可以試著溫柔地看待自己。
(@走進(jìn)奶牛貓是bot類博主,其投稿大多以奶牛貓的語(yǔ)氣對(duì)“人朋友”說(shuō)話。)
這或許就是“上帝視角看人類”的真正功能所在:在這個(gè)情緒持續(xù)外溢、照護(hù)機(jī)制不斷失效的時(shí)代,它為疲憊的個(gè)體騰出了一點(diǎn)點(diǎn)喘息的縫隙,讓我們既不必時(shí)時(shí)堅(jiān)強(qiáng),也不至于完全崩潰。
當(dāng)自我敘述越來(lái)越困難時(shí),一句“人類太好笑了吧”既不是嗲,也不是媚,而是一層輕輕落下的殼。
我們獲得了一個(gè)新的視角。但人類真正的能動(dòng)性,并不止于抽離,而在于來(lái)回切換視角,重新回到生活本身。
(圖片來(lái)源于網(wǎng)絡(luò))